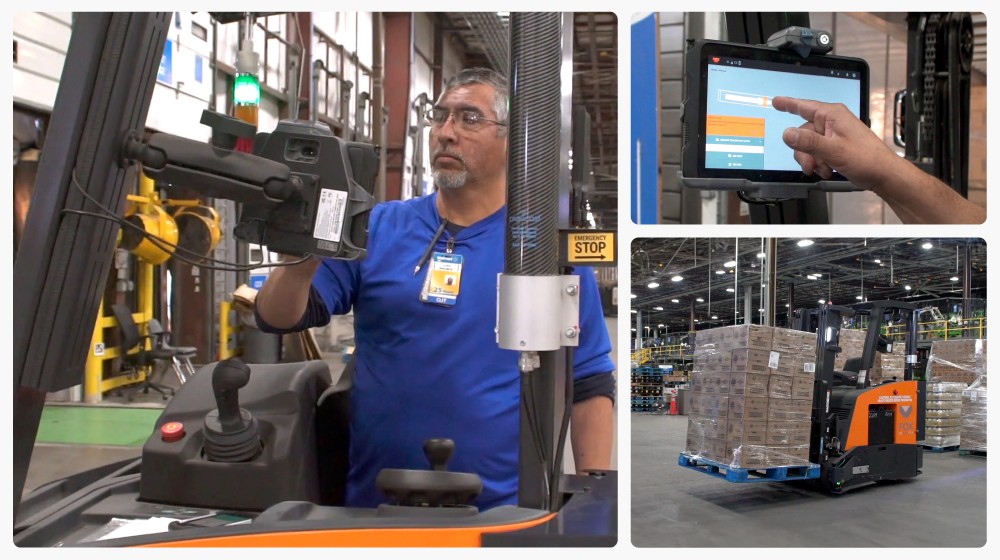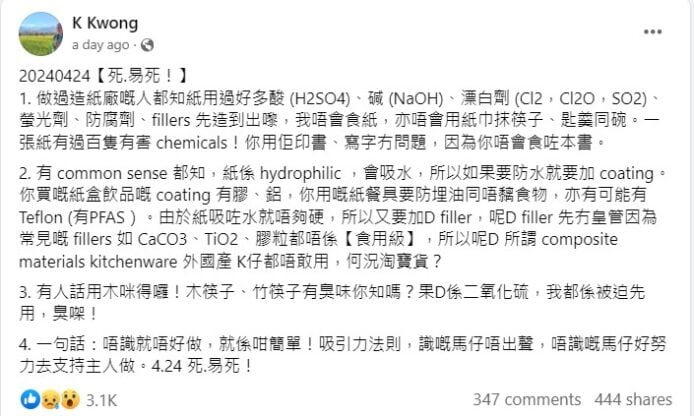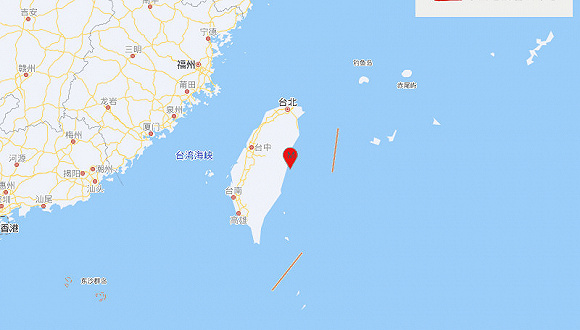三十年前上中学的那会儿,我们三个人在初中同过学,一个班的。那时,各村的学校都只设到五年级,最高到七年级,八年级才刚刚兴起来,村里没有校舍,也没有师资,所以,几个村里上八年级的学生都集中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的中学。这村的中学也没有多余的教室,我们的课堂就临时设在村里的一个大库房。
破败的库房,时常有老鼠出没,吓得女同学的尖叫声,惊慌中窜到屋顶的老橼上,灰尘噗嗖嗖落下来,几只麻雀拖儿带女地四散而逃。这是生产队用过的库房,装粮食用的,小麦,玉米,高梁,小米、黄豆,绿豆。库房没窗,只有两扇厚重的像历史一样的木门,吱呀呀开,吱呀呀合,像夜深人静时老鼠磨牙的声音。教室总是畅开着两扇大门,太阳光低了头能勉强照进来,正午时分,阳光或许能照到讲台的台阶下,爬在最前面最靠近门的一两排女同学的脚背或脚趾上,有时爬在她们光洁的圆润的小腿肚上,亮亮的,贪婪的,女同学的花裙子到显得相形见拙。昏暗的教室里,麻雀腑冲着从拱形的门楣下飞出,再猛地向上拉高,像飞机穿越涵洞的特技表演,一缕烟冲向云天。在这里除了朗朗的书声,我能记起的而且刻骨的,就是关于老鼠和耗子的委屈和笑话。语文课上,老师讲书面语和方言的区别。一只老鼠像道具一样从讲台上旁若无人的走过,迈着日本女人细碎的樱花小步,临下讲台,不忘贼眉鼠眼地瞅了我或其他同学一眼,没有想到的是它竟然给我使了诈,让我出了至今还耿耿于怀的丑。语文老师随口说:同学们,老鼠是方言,还是小耗子是方言?老鼠,我们常常这么叫它,而小耗子的名号却很陌生。平常说的就是方言,平常不多说就是书面语。我对自己的判断很得意,大声说:老——鼠。除我之外,全班的同学都异口同声答道:小——耗——子。我的“老”字发声很大,盖住了“小”字,全班同学的“耗子”发声很大,摭住了我的“鼠”字。站在讲台上的语文老师,一个男老师,黑脸,高个,一下子变了脸,唬着着驴一样长而黑的脸,向讲台下吼道:刚才谁说是“老耗子”?杨进元!站起来!是不是你说的?我站起来,一副没病不怕吃冷馍馍的理直壮,说:不是!我说的是老鼠。他问我左边的女同学,女同学说我说的是“老耗子”,问我右边的男同学,男同学也这么说,结果,全班的同学都证明我说的是“老耗子”。那次人丢大了,黑脸顺手弹出一截正在板书的粉笔头,比飞毛腿导弹还精准,在我小小的鼻尖上爆炸,弹飞到教室门外,像刚刚飞走的麻雀一样。我的鼻尖上白白的一点,小丑一样无地自容更愤愤不平。冤案!
印象中,那只是人生最短暂的一个口岸。一年后,我们参加中考,此后,班里二十几个男女同学都各奔东西,几乎再没有见过面。时间长了,一些名字彻底消失,而一些名字也似有若无,让人觉得那不过是一个梦境,不真实的故事。而事实上,我们真的同过学,大部分人的模样都记得,青涩的,懵懂的,俊俏的,长疤的,黑的,白的,高的,低的,长发的、短发的、光头的,自然卷的,流海的,辫子的,这些记忆怕是在任何的梦境中都不会如此的永不变样。无事的时候,他们一个个都跳出来,像是刻意地告诉我,这是真实的存在。只是更多的时候,他们淡出了忙碌中的平庸,在遥遥的时空中,历史一样绻缩于一隅。
前两年,春花烂漫的时节,县政协换届了,我这个老委员又一次当选。不期在开会的间隙,被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叫住。他个子不高,稍胖,方脸,颜色重,眼睛小而圆,有神,像珠子一样放光,光束很集中。看样子他是新进的政协委员,觉得有些面熟,也觉得有些面生。他说:你不是杨进元吗?我说:是。他显得有些兴奋,像发现了商机一样提神,说:我是沈强啊,王村中学八年级,咱们的宿舍在舞台上,咱俩的地铺挨在一起啊。
生产队的库房被我们当做了教室,前面村里的大舞台就成了我们男生的宿舍。舞台很大,地铺很长,一溜儿排开,靠在北墙根。记得下面是用砖垒起的空心隔层,上面铺了麦秸杆,把被褥往上一放。不知道冬天是怎么过去的,只记得夏夜,晚自习归来,有些人躺下,拿了手电筒照着看书,沈强就是这一种。更多的人疯闹一阵子,说三国的关公赵子龙,说封神的哪吒姜太公,说西游的唐僧妖成精,说到兴头,穿着裤头在台子上亮起架式。月光像如今的聚光灯一样打到舞台上,一场一场的戏拉开,月光也不断地追逐着,记不清是那个同学凌空飞起,又像展翅的老鹰一样落下,然后,钻进被窝,睡觉,打呼噜,梦声和月光星光交融在一起。半夜时分,常常有人起夜,从被窝爬出,光着脚小跑几步,站在舞台边上,一阵痛快,哗哗声飞溅,一条银河从半空中抛物线一样落下,年轻,水足,时长,水珠飞纷,星辉闪耀。
后来,大部分的同学就再没有音信。沈强上了中专,回来在县教育局,我见过一次,他正在练书法,字写得挺像那么回事。再后来,他就不见踪迹,据说是下海了。前几年,县城建起一个高档次的温泉洗浴城,气派很大,生意很好,方圆百十里的老板都到那儿消费。听说洗浴城就是沈强开的,自己当起了老板,但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。这次不期而遇,他摇身变成县政协委员,不是他叫我,我都不认识了。
他说:哎!你知道吗,咱们在王村中学的那个班,还有一个人当上政协委员了。我问是谁,他说是马巧莲。马巧莲,一个像竹竿一样的女同学,没记得和她说过几句话,只记得她爱笑,也没有银铃一样的笑声,微微露出一排瓜子小白牙,消瘦的脸从嘴角开始,花辨一样,一层层绽开,甜美的,羞涩的,内敛的,一点都不热烈,却让你能记住。见到马巧莲时,她就站在我面前,我却不敢相认。这怎么会是马巧莲呢?
三十年前的三个初中同学,一下子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相聚,实在让我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。那个班,总共也就二十几个人刚出头,而全县58万人之也就两百多个委员。私下里,我们都挺得意的:咱那么班厉害吧?
今年春节,沈强坐东,我和马巧莲作陪,联系了十几个从外地回来的八年级同学吃了顿饭。我来得迟些,他们都到了。马巧莲说:你先不要吃,一个个认认同学,叫不上名字的,对不上号的,是男同学的罚你一杯酒,是女同学的罚你三杯酒,结果,我大醉,他们大笑。
其实,人生就是一条条自我的小路,弯弯曲曲的,渐行渐远的,与众不同的,单枪匹马的,只是岁月轮回,沧桑更替,不经意间,在一个想像不到的交叉路口交汇,集合。